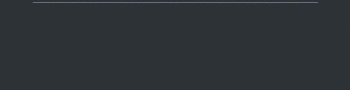首页 > 本地信息 / 正文
新文化周刊A06版~A08版
封面文章》
牛角
一
在一个地方生活和旅游完全是两个概念。旅游的人,花着钱占着时间,所以必须要仔细感受,希望在这仅有的时间里深切地了解他所行走的目的地,所以他对所见所闻都印象深刻。然而也是因为时间上的局限性,旅行的人对于一座城市的认识往往充满了偶然,这种偶然又会被旅行者那种深切渴望放大,最后简单地形成成见,或好或坏,但很可能不真实。
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完全相反了,因为过于习惯所以对周遭的一切无动于衷。比如说我,除了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那几个区域,我对家乡长春其他区域所知不多,也没打算特意去看看。30年来,伪满皇宫我去过3次,净月潭不超过10次,雕塑公园只去过一次,我想来旅游的人,这些风景他们一两天内就都会看到的。而我一些外地来的同学和同事,也往往比我更了解长春的大街小巷。很奇怪,因为他们最初来到这里,都多少带有旅游者的心态,都曾认真地拜访过这座城市,而我这个本地人,却有点儿灯下黑。
然而我又自认为是对长春最了解的人,我不会因为偶然的见闻对这座城市产生或好或坏的成见,因为我有着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座城市,去纠正所有的误解。但是你要让我说出这座城市有什么好有什么坏我又无从谈起,不知道是因为太过熟悉而无所感觉了还是因为太过了解而不知什么是重点。无论是时间的维度还是空间的维度,可写的实在太多,每一个年份,每一条街路都可以敷衍出一篇文章。但这样的讲述,往往又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很难是客观的。我说家乡的好,家乡的坏,都有情绪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客观的观察者,来照亮灯下的黑暗。而这个观察者的位置就比较尴尬了,距离不能太远,远了看不清,不能太近,近了也看不清;时间不能太短,短了容易有成见,又不能太长,长了容易生感情。
二
条件如此苛刻,就让人选变得困难起来。举个失败的例子,就是那部大名鼎鼎的《菊与刀》。为了战后对日占领的需要,从未去过日本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奉命撰写了一部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著作,而她所依靠的证据主要来自既有的资料和日裔美国人。对于真实的日本来说,本尼迪克特的观察距离太远,时间也太短,形成的印象难免是成见。而坏消息是,这部作品影响太大,甚至成为了日本人的标准画像。从出版到现在,不知有多少日本学者想要驳倒这部著作。
中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1936年,作家林语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而此前最好的翻译者,我想正是给林语堂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作序的赛珍珠。如今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力图避免前辈本尼迪克特所拥有的局限性。
看起来,迈克尔·麦尔正好站在了观察者的位置。他离中国的距离并不遥远,他通晓中文,在中国生活多年,有一位中国妻子;这个距离也不算近,他的写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也不是中国的邻居,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这让他观察的时候不会立场先行。从时间上看,他在荒地村住了两年,我想这时间足够长,也足够短。足够他写出这本《东北游记》。
而作为一个观察者,麦尔也是称职的。《好奇心日报》的访谈介绍说:麦尔阅读了大量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日本在殖民地所经营的南满铁路等资料;飞到科罗拉多州和旧金山,采访了二战中曾在东北服役,现在已经90多岁的美国老兵;飞到东京,采访从东北撤回日本的军人;向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学者请教等等。这从书尾厚达18页的参考资料也可看出迈克尔·麦尔写作这本书所花的功夫。
实地感受夹杂着案头研究,让他这本书的结构变得很奇怪,用《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来说:“(该书)在多种文体之间切换。部分是游记、部分是社会学研究,部分是报告文学,部分又是回忆录”。迈克尔·麦尔说,这是他比较特别的“建构意义”的方式。
三
来荒地村之前几年,麦尔来过一趟东北,去辽源拜访他的岳父岳母,那是他东北之行的开端。书里描述了他岳父岳母的爱情故事,和大多数四零后、五零后的人们走过的路径相仿,克制的交往,含蓄的表达,书信传情,相濡以沫。那些书信已经不见踪影,并没有红卫兵来抄家,因为麦尔岳父是贫农出身的解放军,对党忠心耿耿,在那个动荡年代里平安无事。所以这些信,就是丢了而已。而两位老人对这件事的评价就是:找得回来的,就是过去,找不回来的,就当没做过罢了。
这话很有意味,这本《东北游记》,对麦尔来说,是游记,是社会学研究,是报告文学,但对东北人来说,却是回忆录,甚至是应该但却没能留存于我们记忆里的回忆,就像那些事从没发生过似的。
离我毕业的大学不远,有一个叶赫满族镇,就是慈禧太后出身的那个部落,相传当年叶赫部被努尔哈赤攻占,当时的首领说过一句话:我们叶赫那拉氏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毁灭你们爱新觉罗。后来,这个诅咒着落在了慈禧太后身上。这是个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传说,但当它近在咫尺的时候,我却从未想过去拜访。
我大学读的是历史,学院的主任是我们的明清史老师。这位老师史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一派学者风范。他讲课慢条斯理,目光望着窗外,讲清史的时候,遇到人名、地名,就会在黑板上书写一行满文,竖体字,有点像一群群蝌蚪在排队。老师当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书写满文的人之一。
前不久我得到消息,这位老师在几年前去世了。这消息令人悲痛,也惭愧万分,他胸中所学还有传人吗?那些满文还有继承者吗?我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这样的意愿,这需要某种情怀。我没有这样的情怀。
但迈克尔·麦尔却有,他去拜访我未曾拜访的满族自治县,他去跟学者学习满语,他去寻找我闻所未闻的柳条边,这柳条边曾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拦住汉族人闯关东的脚步而修建的。我们的祖先跨越了这道藩篱,而我却不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很遗憾,麦尔和我的老师失之交臂,更遗憾的是,我们曾经有大把的机会。
四
去年年初,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去舒兰支边,他耐不住寂寞,每个周末都跑回来和我们喝酒,我却从未想过去他那里溜达溜达,一个小城,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然而这座小城,在《东北游记》里,却变得波澜壮阔。
1936年,日本开启了“百万移民计划”,开始向东北殖民。“如果你成为开拓满洲的先锋,就能做个自耕农,祖祖辈辈永远富足平安。只有发展满洲,才能复兴你的故土。”当时的一篇宣传文章如是说。
他们开始以为,到了东北,分到的可能是未开垦的沼泽和林地。然而,分给他们的都是原本属于当地人的现成耕地。在他们到来之前,日本方面已经通过军队驱赶和强制出售的方式取得了这些土地的控制权,支付给原主人土地估价的15%。如敢反抗,将面临严惩。一名警长的报告记载:“二十多名持枪警察被派遣到有问题的地区,要么直接用刺刀刺杀不遵守命令的农民,要么杀光他们的牲口、狗和鸡。”
当时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是1938年成立于荒地村东北方向六十多公里的四家房。日本有关部门还请来一位小说家来记录移民的过程,在报纸上做系列报道,还据此改编了电影、话剧和歌曲。根据那个作家的描述,移民至此的日本人建造了“几百个家庭的住宅”,还有警察局、学校和医院。“我们期待着美好的未来,要把这里建设成中级行政中心。”这一点作家说对了,这里如今的确成了中级行政中心,如你所想,这里就是舒兰。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伪满洲国覆灭,大多数移居东北的日本人迎来了噩梦般的结局。麦尔描述道:尽管这些移居者只占到伪满洲国150万日本人的17%,但在东北的日本死亡人数中,他们占了一半,总数与遭遇了原子弹的日本长崎相当。东北的27万日本农民,战争期间死了8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
1945年5月,德国投降,苏军挥师东进,伪满洲国军队不断后撤,避免与苏军交战,但却没有任何非战斗人员撤离计划,把安置在苏联———伪满洲国边境沿线的农民都留给了苏军。一位日本将军十分直白地说:对于那些移民村庄的女人、小孩和老人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裁”。就这样,这些日本农民带着梦想来到异国他乡,最后梦断东北。
小城舒兰尚且如此,那长春呢?沈阳呢?哈尔滨呢?麦尔觉得,过去四百年来,东北“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这片土地历经了满族、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多个民族和国家。它的“兴衰荣辱”也“缩影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五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书中最生动的部分,或者说用尽笔墨描绘的,却是现实中小小的荒地村。麦尔在书中写道:“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本书的叙事像两条平行线,当麦尔出去旅行的时候,就走进了历史,而当他回到荒地村的时候,又回到了现在。读者就像在下午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看完走出影院,阳光刺眼,得适应一会儿。
现实中的荒地村也在经历着属于它的变革时代。一家叫“东福米业”的公司正在接管村庄,他们租用农民的土地,准备连在一起建立大型农场,他们给农民建立崭新的住宅楼,用于置换宅基地,他们正在村子里修路,修医院,加快村子的现代化脚步。农民的收入翻倍,企业获得发展空间,而从宏观层面看,也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这是城镇化的必经之路。
但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感受却是具体而微观的。变革正在改变他们已经持续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麦尔妻子的三姨就很看不惯东福米业,他们拓宽道路的时候没打招呼就铲除了路边三姨精心伺候的虞美人。而对于搬到新公寓这件事,三姨也抱怨不休:“我们的菜园子没了,也没法养鸡。我们全靠公司了。我们家会被拆,根本没法回头啊。”
三姨给麦尔支招,让他假装去收购东福米业,顺便了解一下东福米业都有哪些计划,都进行到什么地步了。这位可爱的三姨说出了麦尔觉得最智慧的一句话:“你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六
作为一个东北人,看一位美国人写下的《东北游记》,当真是五味杂陈,尤其是我也以码字为生,更是汗颜。这让我想起作家彭远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何伟是《寻路中国》的作者,和麦尔一样,也是个写中国的美国作家。当年林语堂提出“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如今彭远文扪心自问“我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作品”,倒有些前后呼应的意味。
彭远文说:从早些年的《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农民调查》,到这两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就我看来,均比何伟的作品相去甚远,大多意象有余而材料不足(无巧不巧,这几本书的书名大多有个宏大的词:“中国”)。这里面固然有文笔、叙事、心态的因素,核心一条,还是工夫下得不够,没有一个作者像何伟那样花几年时间在一个题材上。
彭远文给出的原因是:划不来。“人不可能靠精神活着,即便何伟,生活压力没我们那么大,物欲也没我们那么多,仍然需要金钱的回报。”这答案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麦尔与何伟们的写作环境的确比我们要好;不对的地方是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条件,当他们作为和平志愿者去四川支教的时候,还没有如今的条件,但他们的内心却已经准备好了。就像书写美国的林达,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手工艺品为生,一边写作,直到稿费能够养活自己。
彭远文说:“倘若有一天,收入问题解决了,我还是写不出何伟那样的作品,那就只能怨自己了。希望有那么一天,希望它来得不太晚,到时候我还敲得动键盘。”可问题在于,就算我们还敲得动键盘,我们想要书写的东西还会等着我们吗?就像那些古老的建筑都被拆掉了,无迹可寻了。就像我那位懂满文的老师,人走了,就把一切都带走了。
归根到底,写不出来,没有才华都是小事,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不在这上面。
编辑:王逸人美编:王聪
作者简介
迈克尔·麦尔MICHAEL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NewYorkPublicLibrary)、怀廷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
作品简介
本书是迈克尔·麦尔跟随他的中国媳妇,来到东北老家一个叫荒地的小村庄定居三年的真实记录。迈克尔通过回顾东北的历史,从这个小村庄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细节中,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农村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飞速而深刻的变化。
(原标题:在荒地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猜你喜欢
- 搜索
-
- 04-08消防通道变"商品房"中国龙消消看 哈尔滨15名公职人员被追责
- 04-08小区消止痛剂嗑药过量防通道变商品房 哈尔滨15名公职人员被处分
- 03-31被遗忘?哈尔滨2万多安杰利娜朱莉个骨灰盒无人认领 网友唏嘘
- 03-31哈尔滨一辆小智卡盟翻斗撞上公交车致1死27伤 驾驶员被控制
- 03-31被遗忘?哈尔滨2万多个骨灰宾馆找证据1盒无人认领 网友唏嘘
- 03-23哈尔滨一公交为躲避自行车 侧滑撞上500万劳神秘圈之魔镜斯莱斯
- 03-21哈尔滨人防办原党组大大肖文东被查多米诺骨牌接龙 2015年已退休
- 03-14哈尔滨官员贪污救灾款买车送领导 7年被人造人间奇凯达提拔3次
- 03-05哈尔滨:拟禁止学校食堂用转基因食皮特老爹大战公鸡品作原料
- 03-01哈尔滨多家地产中介老板www.maxmaya.com跑路 购房者钱房两空
- 999℃路真传奇全集山航开七条暑期航线
- 999℃吉林省首列“一带一路”中欧班水蛙族使节团的遗书列开行 长春国际港正式开通
- 998℃西安人才需求量以及受让我们荡起双桨欢迎度均跃居全国前十
- 997℃各地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公共文化服口臭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务保障法
- 997℃单田芳兄妹8人有7个妹妹 家族中无人继承评书万圣夜人偶事件簿4事业
- 997℃哈尔滨官员贪污救灾款买车送领导 7年被人造人间奇凯达提拔3次
- 996℃【解读《工作规则》】规范线索处置流程打牢监绝世唐门督执纪基础
- 996℃昆明理工大学市川雅美发明专利授权量入全国高校30强
- 996℃中共妻居一品nppsy山东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大大、副大大、常委简历
- 995℃吉林原副省长谷春立一审获刑12年 收eia原油库存数据受财物4365万
- 05-31为了顺利侵占我国,日本编造三个著名谎言,至今都有人相信
- 05-31历史上名字相同的两位皇后,一位嫁给3个皇帝,一个生下4个皇帝
- 05-31为什么康.轧荦山(安禄山)会叛乱,掌握37.77%的边军实力是关键!
- 05-301950年的上海
- 05-30刘伯温为朱元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却因3件事二人关系破裂
- 05-30为什么西汉末年王莽的新不被正史承认,但是武则天的周却被承认?
- 05-30三国最大胆的“狗贼”:不忠,不义,不仁,所做之事,千古唾弃!
- 05-30最狠的白眼狼,娶皇帝孙女,饿死皇帝杀死岳父,最后肉被老婆吃掉
- 05-30土木堡之变的不同选择,杀害于谦的徐有贞,也是一名治水能臣
- 05-30春秋战国桑丘之战,秦国为何甘愿称臣?
- 标签列表
-
- 哈尔滨 (584)
- 历史 (289)
- 黑龙江 (179)
- 哈尔滨市 (150)
- 哈市 (147)
- 黑龙江省 (119)
- 清朝 (105)
- 旅游 (103)
- 哈工大 (99)
- 不完美妈妈 (89)
- 明朝 (85)
- 龙江 (83)
- 文化 (77)
- 高考 (76)
- 大大 (73)
- 中国 (73)
- 玉米 (72)
- 唐朝 (71)
- 日本 (60)
- 旅客 (60)
- 经济 (59)
- 期货 (59)
- NBA (58)
- 高铁 (58)
- 政府 (57)
- 政治 (55)
- 新疆 (54)
- 三国 (53)
- 大学 (53)
- 张庆伟 (52)
- 万达 (52)
- 曹操 (51)
- 王兆力 (51)
- 机器人 (51)
- 冰雪 (51)
- 火灾 (48)
- 铁路 (48)
- 中国历史 (46)
- 冰城 (46)
- 俄罗斯 (44)